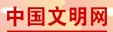紙頁上的夏天(陳興明)
發布時間:2025-06-08 09:28:00 信息來源:江西省交通投資集團南昌南管理中心 瀏覽次數:
今年高考首日,我路過小區旁的考點,遠遠便聽見警戒線外的喧嘩。穿白襯衫的考生攥著準考證往樓里跑,家長們踮著腳張望,有個穿藍布衫的中年女人正幫女兒理衣領,指尖沾著點面粉——像極了三十年前那個清晨,我媽站在梧桐樹下,替我理平校服領口時,手背蹭到的灶臺灰。風掀起她的傘面,我忽然就聞見了記憶里的豆香……
教室的老吊扇轉得慢,鐵皮葉片磨得發亮,轉起來時嗡嗡響,撲簌簌往下掉銹渣,像誰撒了把細鹽。我趴在課桌上數倒計時,紅漆數字從“100”退成“30”那天,后窗的梧桐葉開始翻卷,風里裹著槐花香,混著教室后排張嬸賣的橘子冰棍味——那是五月底,蟬鳴剛起,日頭毒得很。
后桌阿杰的課桌總比別人亂。他用圓規在桌角刻了個“過”,說這樣就能逢考必過。桌邊的草稿紙是從《人民日報》上裁的,邊角卷著毛,演算步驟擠成一團,像被揉皺的云。可每次模考后,他都把錯題本推過課桌縫:“這道立體幾何,你看輔助線是不是該從這兒引?”他的鋼筆是英雄牌的,筆帽磕掉了漆,寫起字來洇紙,卻把每個步驟都描得極清楚。
走廊里的倒計時牌掛在傳達室門口,值日生每天用紅粉筆描一遍,粉筆灰落在過廊的水泥地上,被我們踩成星星點點。班主任李老師總在早自習前站在門口,手里攥著搪瓷缸,看著我們早讀。他的藍布衫第二顆紐扣總系不牢,風一吹就晃,露出里面洗得發白的秋衣——后來才知道,那是他嫁女兒時穿的,女兒在外地念大學,去年寄了件黑色毛衣,他總說“穿著熱乎”。
高考前三天,教室開始清場。我們把課本搬去圖書館,木頭課桌在地上拖出刺耳的響,紙箱堆得比人高,封條撕下來時簌簌響,像在揭一張舊日歷。阿杰摸著空了的課桌說:“你說,這些桌子會不會記得咱們?”陽光透過窗戶斜照進來,照見他校服膝蓋上的補丁——那是上周體育課摔的,他說等高考完,讓老家的奶奶用藍布補塊新的。
考試那天下著太陽雨,我踩著一路的水漬進考場。第一場考語文,作文題是“時間的容器”。我盯著試卷上的空白處,忽然想起教室后墻的黑板報,每月換一次主題,春天是“春芽”,秋天是“金穗”,最后一個月是“追夢”。粉筆灰落在黑板槽里,積成小小的丘,像時光的繭,又像我們藏在課桌里的小秘密——阿杰藏過半塊橘子硬糖,我用玻璃彈珠跟他換過。
第一場語文完后,走出考場,看見媽媽站在梧桐樹下,手里提著綠漆鋁桶,傘歪向一邊,半邊藍布衫都濕了。她看見我,慌忙把傘扶正,說:“豆漿熱的,喝兩口。”鋁桶蓋兒一掀,豆香混著熱氣撲出來,我捧著搪瓷碗喝,燙得直吸氣。媽媽的手背上沾著洗鍋的黑灰,指節粗粗的,像老樹根——她凌晨三點就起來磨豆子,石磨轉得慢,手腕都酸了。
考完最后一門數學,鈴聲響得脆生生的。同學們涌出考場,有人抹眼淚,有人拍彼此后背,沒人扔課本——那時候課本金貴,要帶回家給弟妹用,或者賣給收廢品的老頭換冰棍錢。阿杰追上來拍我肩膀:“我就說那道圓錐曲線能對吧?”他的校服被雨淋濕了,貼在背上,藍白格子暈成一片,像片被打濕的天空。我們站在教學樓前的臺階上,看夕陽把梧桐葉染成金紅色,風過時,滿地都是碎金,混著冰棍紙的反光。
放榜那天,我在老家的院子里剝毛豆。外婆把煮好的綠豆湯端來,粗瓷碗沿沾著茶漬。傳達室的公用電話響了,是班主任李老師的聲音,帶著點鄉音:“考上了,考上南昌大學。”媽媽正在擇菜,手里的空心菜“啪”地掉在地上。她彎腰去撿,我看見她后頸的白發,像落在青石板上的雪——那時候她才四十歲,可操勞早把頭發染白了。
后來整理木箱,翻出當年的錯題本。牛皮紙封面卷了邊,阿杰的圓規印還在,深深刻在“解析幾何”那頁,像道淺疤。李老師的搪瓷缸蓋還卡在夾層里,缸身有幾道裂紋,是他當年給我們熱牛奶時燙的。媽媽的豆漿漬已經暈成深褐的云,浸在紙頁里,怎么也洗不掉。
如今我常夢見教室的老吊扇還在轉,鐵皮葉片嗡嗡響,掉著細銹渣。阿杰舉著英雄鋼筆說“看這個輔助線”,李老師的藍布衫紐扣在風里晃,媽媽站在梧桐樹下,傘歪向一邊,手里提著綠漆鋁桶,豆香混著熱氣漫過來。那些被折疊在三十年前夏天里的時光,原來從未褪色——它們長成了我骨血里的光,在每一個需要勇氣的日子里,輕輕托著我,往前走。(玉山收費所)
教室的老吊扇轉得慢,鐵皮葉片磨得發亮,轉起來時嗡嗡響,撲簌簌往下掉銹渣,像誰撒了把細鹽。我趴在課桌上數倒計時,紅漆數字從“100”退成“30”那天,后窗的梧桐葉開始翻卷,風里裹著槐花香,混著教室后排張嬸賣的橘子冰棍味——那是五月底,蟬鳴剛起,日頭毒得很。
后桌阿杰的課桌總比別人亂。他用圓規在桌角刻了個“過”,說這樣就能逢考必過。桌邊的草稿紙是從《人民日報》上裁的,邊角卷著毛,演算步驟擠成一團,像被揉皺的云。可每次模考后,他都把錯題本推過課桌縫:“這道立體幾何,你看輔助線是不是該從這兒引?”他的鋼筆是英雄牌的,筆帽磕掉了漆,寫起字來洇紙,卻把每個步驟都描得極清楚。
走廊里的倒計時牌掛在傳達室門口,值日生每天用紅粉筆描一遍,粉筆灰落在過廊的水泥地上,被我們踩成星星點點。班主任李老師總在早自習前站在門口,手里攥著搪瓷缸,看著我們早讀。他的藍布衫第二顆紐扣總系不牢,風一吹就晃,露出里面洗得發白的秋衣——后來才知道,那是他嫁女兒時穿的,女兒在外地念大學,去年寄了件黑色毛衣,他總說“穿著熱乎”。
高考前三天,教室開始清場。我們把課本搬去圖書館,木頭課桌在地上拖出刺耳的響,紙箱堆得比人高,封條撕下來時簌簌響,像在揭一張舊日歷。阿杰摸著空了的課桌說:“你說,這些桌子會不會記得咱們?”陽光透過窗戶斜照進來,照見他校服膝蓋上的補丁——那是上周體育課摔的,他說等高考完,讓老家的奶奶用藍布補塊新的。
考試那天下著太陽雨,我踩著一路的水漬進考場。第一場考語文,作文題是“時間的容器”。我盯著試卷上的空白處,忽然想起教室后墻的黑板報,每月換一次主題,春天是“春芽”,秋天是“金穗”,最后一個月是“追夢”。粉筆灰落在黑板槽里,積成小小的丘,像時光的繭,又像我們藏在課桌里的小秘密——阿杰藏過半塊橘子硬糖,我用玻璃彈珠跟他換過。
第一場語文完后,走出考場,看見媽媽站在梧桐樹下,手里提著綠漆鋁桶,傘歪向一邊,半邊藍布衫都濕了。她看見我,慌忙把傘扶正,說:“豆漿熱的,喝兩口。”鋁桶蓋兒一掀,豆香混著熱氣撲出來,我捧著搪瓷碗喝,燙得直吸氣。媽媽的手背上沾著洗鍋的黑灰,指節粗粗的,像老樹根——她凌晨三點就起來磨豆子,石磨轉得慢,手腕都酸了。
考完最后一門數學,鈴聲響得脆生生的。同學們涌出考場,有人抹眼淚,有人拍彼此后背,沒人扔課本——那時候課本金貴,要帶回家給弟妹用,或者賣給收廢品的老頭換冰棍錢。阿杰追上來拍我肩膀:“我就說那道圓錐曲線能對吧?”他的校服被雨淋濕了,貼在背上,藍白格子暈成一片,像片被打濕的天空。我們站在教學樓前的臺階上,看夕陽把梧桐葉染成金紅色,風過時,滿地都是碎金,混著冰棍紙的反光。
放榜那天,我在老家的院子里剝毛豆。外婆把煮好的綠豆湯端來,粗瓷碗沿沾著茶漬。傳達室的公用電話響了,是班主任李老師的聲音,帶著點鄉音:“考上了,考上南昌大學。”媽媽正在擇菜,手里的空心菜“啪”地掉在地上。她彎腰去撿,我看見她后頸的白發,像落在青石板上的雪——那時候她才四十歲,可操勞早把頭發染白了。
后來整理木箱,翻出當年的錯題本。牛皮紙封面卷了邊,阿杰的圓規印還在,深深刻在“解析幾何”那頁,像道淺疤。李老師的搪瓷缸蓋還卡在夾層里,缸身有幾道裂紋,是他當年給我們熱牛奶時燙的。媽媽的豆漿漬已經暈成深褐的云,浸在紙頁里,怎么也洗不掉。
如今我常夢見教室的老吊扇還在轉,鐵皮葉片嗡嗡響,掉著細銹渣。阿杰舉著英雄鋼筆說“看這個輔助線”,李老師的藍布衫紐扣在風里晃,媽媽站在梧桐樹下,傘歪向一邊,手里提著綠漆鋁桶,豆香混著熱氣漫過來。那些被折疊在三十年前夏天里的時光,原來從未褪色——它們長成了我骨血里的光,在每一個需要勇氣的日子里,輕輕托著我,往前走。(玉山收費所)
上一篇:收費大棚下的故事(管麗榮)
下一篇:最后一頁